原创 沈从文的虎耳草
作者:黎荔

虎耳草是我见过最萌的植物,因其叶圆大、形如虎耳而得名,个人感觉它可可爱爱的。如果你见过这种小草,就知道它的叶片极为特别,一茎一叶,叶子心形,边缘有细致的小齿,正面翠绿作底,白色的长条斑纹,背面红紫色。叶片大小近似铜钱,又像是小荷叶那般圆润,而从整体轮廓看,竟与老虎的耳朵极为相似,这也是它得名“虎耳草”的缘由。老虎的屁股摸不得,那就摸老虎的耳朵吧!摸摸这植物界难得的小可爱,那毛茸茸的叶片摸起来热乎乎的,也许因为毛茸茸,所以给人热乎乎的错觉,确实有小动物的质感。
自从看了沈从文先生写的《边城》,我便认识了虎耳草,书中的翠翠在梦里采摘了虎耳草。这是《边城》最美妙的细节,情窦萌动的纯真少女翠翠,在追求她的少年傩送为她唱山歌的朦胧月夜,“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,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,上了白塔,下了菜园,到了船上,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——去作什么呢?摘虎耳草!”翠翠在梦中恍兮惚兮采摘虎耳草,这株小小的植物承载了她懵懂的爱情,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。阅读《边城》,总有什么是永远不能用语言进行实实在在的描述的,就是那个氛围,人世辽远,岁月悠长,湘西山水青翠,烟雨氤氲如雾,沈从文的文字如罂粟般使人昏昏欲睡。读者一进入《边城》,将会由始至终甘心情愿或不由自主地任它所迷乱,被带到一种明净又虚茫的氛围中。
《边城》中,沈从文将自然写成一个浸透感情的旋律波动:边城女儿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,把皮肤变得黑黑的,触目为青山绿水,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。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,为人天真活泼,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。她镇日长闲在大岩石上晒太阳,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,在深翠逼人的两山间拉船过渡,仰头望着崖上那些肥大的虎耳草,在溪河上、渡船上悲欣交集地生息……翠翠自然纯朴又空灵缥缈,整个环境安寂又澄澈,仿佛只有暴风雨才能撼动边城世界的悠长梦寐。如果要用什么景物点缀在翠翠的身边,当然要符合翠绿的自然之色,所以除了渡船下豆绿色的河水,清澈纯净,不染尘灰,翠翠身边还有许多郁郁葱葱的植物:篁竹、胡葱、青豆、青桃……还有悬崖上的虎耳草。

虎耳草广泛分布于华东、中南、西南及河北、陕西、甘肃等地,喜阴凉潮湿、土壤肥沃的环境,常生于海拔400-4500m的林下、灌丛、草甸和荫湿岩隙。如果你想去寻它,摸摸它的耳朵,可以去林下、灌木丛,草甸和阴湿岩缝碰碰运气,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但是,应该我们寻到的虎耳草,都不及《边城》中的虎耳草,因为那是翠翠的虎耳草,梦中的虎耳草。
梦外,翠翠大清早提着篮子去小山后掘竹鞭笋,带回的除却十来根小小鞭笋,还有一把大的虎耳草。在《边城》的字里行间呼吸领会,我想象虎耳草在湘西的雨季里,会格外茂盛起来。溪边、石隙、河岸的陡坡上,处处皆可见它一片片圆而带心形的叶子,俯仰在湿润的泥土里。叶背一层白茸茸的细毛,湿气凝成了水珠,便缀在绒毛间,颤巍巍地发亮,如无数微小眼睛,静默地观望着这风雨飘摇的世界。
翠翠在溪边洗菜时,应该常常能看见这种草。她蹲下身子,目光从菜叶滑至溪畔,只见虎耳草繁密地长在湿润的石缝里,叶片厚实而碧绿,叶缘微微卷曲,显出一种饱满的生命力。有时,她忍不住伸出湿漉漉的手,轻轻抚过那叶背的绒毛,茸茸的触感竟仿佛透过指尖,直抵心尖,痒丝丝的。翠翠便悄然缩回手,垂了头,耳根处微微泛起一点红晕来,仿佛被人窥破了心底潜藏的秘密——那草叶的茸茸,竟仿佛一种羞怯的体触,在无声无息间叩问着少女初萌的情怀。
河岸边上,虎耳草也生得尤为繁盛,它们依偎在粗砺的石块间,无论风起浪涌,只管安稳地守住自己足下一方微小的泥土。叶面上密布着细小的脉络,如一张张无声的网,滤过喧嚣的风声雨声,只留下溪水长流的絮语;它们那不起眼的小花,白色里透出微红,一簇一簇在绿意中探出头来,不张扬,也不瑟缩,只是寂静地开落——仿佛时光的节拍,只在无人注目处默默点检着生命。若逢连日阴雨,溪水涨满,浑黄的浪头拍打着岸石,虎耳草便整个浸在浑浊的水里了。浪退之后,叶片上沾满泥点,湿漉漉地贴伏于石面,然而不过几日,待到阳光刺破云层,叶子便又舒展开来,洗去泥痕,依旧青翠照眼。生命之韧,便在这泥水冲刷与阳光救赎之间,往复显现,无惧无惊,只管生息。
记得汪曾祺回忆沈从文的文章不少,其中一篇《星斗其文,赤子其人》——篇名当然来自张充和用小楷为沈从文写的挽辞:“不折不从,亦慈亦让;星斗其文,赤子其人”——写沈从文少数民族血液里的蛮劲,写他凡事的“耐烦”,写他对家乡的感情,他的交游,他对文物的痴心,他日常生活的朴素,最后写到他极为简单的丧事。末了话锋一转,思绪似乎很突兀地跳到一种草上:“沈先生家有一盘虎耳草,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盘里。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。这就是《边城》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,沈先生喜欢的草。”
据说汪曾祺提到的那盘虎耳草,是沈从文从家乡带回的,在北京的家里长得很好。田时烈《家乡人迎葬沈从文》一文中专门写过,沈从文一九八二年回家乡凤凰,小船在杜田的凉水井旁边靠岸后,沈从文上岸去看了虎耳草,“井旁岩壁上长满了茸茸的‘虎耳草’,沈先生告诉我们‘虎耳草’很能适应各种土质,开小白花,是消炎去毒的一种好药。”也许在沈先生心目中,这可可爱爱的虎耳草,就是翠翠的小小生命的化身。山野女儿翠翠,本身就如这自然之物那样单纯自在,天真活泼。我猜在沈先生的精心照顾下,他家的虎耳草叶子长得胖墩墩的,繁盛无比,四处蔓延,把花盆的泥土遮得严严实实。长着长着,虎耳草有花苞了。不久虎耳草开出了一朵花儿,观赏清新小白花的同时,沈先生也会轻柔地摸摸虎耳草(老虎的耳朵)吧?尤其当他的手指触碰到叶背茸毛上微颤的水珠,就如同沉静而执拗的泪滴——浸染着人间岁月里的凄清与希望,也浸染着他无法言说、却兀自生长的心事。
日子过去,生命如草,枯荣有时,湘西故乡终究再没有等到那个赤子的归来。只有高高的山崖石隙里的虎耳草,年复一年,依旧在风雨里生长着,翠绿依然。虎耳草不言语,却以最朴素的荣枯轮回,默默告谕着这世间恒常与变幻的哲理。草叶无眼,却仿佛比人看得更远:生命之存在,不在风浪中随波逐流,而在根须紧握泥土的那份寂静里,在无言的绿意中,安然迎送人间的风霜雨雪。
资讯
推荐
- 药材资讯
- 中药养生
- 农村山间神奇草药萝藦果,化痰止咳,补虚助阳,全身上下都是宝
- 38种生长在农村的中草药(有图解),天天踩它,却不知它的神奇功效
- 萝藦的功效与作用及禁忌
- 有毒、有小毒、有大毒的所有中药材汇总
- 寓意好价值高,人称“吉祥草”,既是花卉也是药,养在家里好处多
- 抗性杂草~铁苋菜(附防除办法)
- 500余种中草药图
- 穿心莲的功效与作用,穿心莲的正确吃法
- 想吃吗?柳州一医院出售中药奶茶!还有中药牛肉面,中药蛋糕、包子.....
- 【中草药介绍】 大飞扬草 性味功效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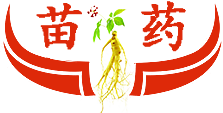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我要咨询(留言后专人第一时间快速对接)
已有 1826 企业通过我们找到了合作